期刊VIP學(xué)術(shù)指導(dǎo) 符合學(xué)術(shù)規(guī)范和道德
保障品質(zhì) 保證專業(yè),沒有后顧之憂
期刊VIP學(xué)術(shù)指導(dǎo) 符合學(xué)術(shù)規(guī)范和道德
保障品質(zhì) 保證專業(yè),沒有后顧之憂
來源:期刊VIP網(wǎng)所屬分類:城市管理時(shí)間:瀏覽:次
摘要:聚居在特定空間范圍內(nèi)的外來人口是我國特大城市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,這一特殊社會群體的“非均衡高度集聚”必然要求大都市區(qū)空間資源配置和結(jié)構(gòu)組織模式作出回應(yīng)。在“人民城市人民建,人民城市為人民”重要發(fā)展理念指導(dǎo)下,有必要對上海市外來人口的空間集聚過程進(jìn)行階段性的總結(jié),為新一輪人口普查背景下的城市管理提供借鑒與參考。基于五普和六普的人口數(shù)據(jù),揭示了2000~2010年上海市外來人口的空間分布及其演變特征,并從經(jīng)濟(jì)、社會和政策等方面討論外來人口空間集聚的影響因素,對上海市城市空間結(jié)構(gòu)優(yōu)化以及外來人口服務(wù)提升提出政策建議。
關(guān)鍵詞:特大城市;外來人口;空間集聚;影響因素;政策建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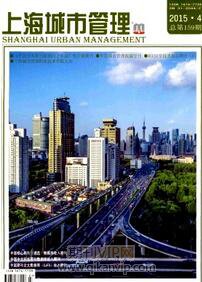
引言
2019年,習(xí)近平同志在考察上海時(shí)提出“人民城市人民建,人民城市為人民”的重要理念,對新時(shí)代上海城市建設(shè)與管理提出了新使命和新要求。城市是一個(gè)生命有機(jī)體,上海作為超大城市,人口總量和建筑規(guī)模更加龐大,生命特征更加復(fù)雜,其中外來人口作為城市建設(shè)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,同時(shí)也是城市管理中不容忽視的重要對象,因而更應(yīng)當(dāng)在新時(shí)代上海“人民城市”的建設(shè)中予以重視。
隨著特大城市的高擁堵、高房價(jià)、空氣污染等“大城市病”日益嚴(yán)峻,不斷增長的人口規(guī)模被看作是城市問題的根源,上海、北京等地都已制定嚴(yán)格的人口控制政策①。實(shí)際上,聚居在特定空間范圍內(nèi)的外來人口是我國特大城市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。在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等一線特大城市,集聚了約1億外來人口,其總?cè)藬?shù)與本地戶籍人口相當(dāng)。以上海為例,2019年末,上海全市常住人口總數(shù)為2 428萬人,其中戶籍常住人口1 450萬人,外來常住人口977萬人。更重要的是,外來人口的就業(yè)類型、居住選擇、交通出行、消費(fèi)行為等方面與本地戶籍居民具有較大的差異性,這使得外來人口的空間行為軌跡與本地人口不同。并且,外來人口傾向于形成空間聚居區(qū)(或是社會區(qū)),而不是在全市范圍內(nèi)的均衡分布。
因此,外來人口這一特殊社會群體在城市中的“非均衡高度集聚”必然要求城市在空間資源配置和結(jié)構(gòu)組織模式等方面作出回應(yīng)。與此同時(shí),外來人口的空間集聚也會反作用于大都市空間組織的效率水平。現(xiàn)有的公共管治政策中,通常傾向于直接采用行政干預(yù)的手段,如戶籍準(zhǔn)入制度,中心城區(qū)內(nèi)對群租房、路邊攤販的取締,機(jī)動(dòng)車車牌拍賣搖號,以及住房限購等。上述政策雖然見效快,但其效果卻難以持久,并且頻繁使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預(yù)要素的市場配置機(jī)制也存在一定的風(fēng)險(xiǎn)。與此相對,政府通常會低估空間系統(tǒng)本身的問題及空間治理的潛力。
筆者認(rèn)為,對特大城市人口的治理,主要是對外來人口規(guī)模快速增長和空間集聚的治理,其目標(biāo)應(yīng)該是通過空間政策干預(yù),優(yōu)化大都市區(qū)產(chǎn)業(yè)、人口、交通、設(shè)施的空間布局,提高空間要素和空間結(jié)構(gòu)的組織效率,使得外來人口在大都市區(qū)內(nèi)實(shí)現(xiàn)合理均衡布局,避免因外來人口過度集聚帶來空間錯(cuò)配和空間運(yùn)行低效的問題。
本文在國內(nèi)外相關(guān)研究基礎(chǔ)上,基于上海市五普和六普的人口數(shù)據(jù),揭示了2000~2010年上海市外來人口的空間分布及其演變特征,并從經(jīng)濟(jì)、社會和政策角度討論外來人口空間集聚的影響因素,旨在為上海市空間結(jié)構(gòu)調(diào)整優(yōu)化以及外來人口社會管理提供政策建議,實(shí)現(xiàn)從空間治理到社會治理。
一、相關(guān)研究綜述
流動(dòng)人口的空間集聚以及與城市主體居民的隔離是世界城市化進(jìn)程中的一個(gè)普遍現(xiàn)象。[1]國外相關(guān)研究多從移民的社會階級和種族視角對隔離產(chǎn)生的原因進(jìn)行分析,主要論述包括經(jīng)濟(jì)、社會和政策三個(gè)方面。例如,經(jīng)濟(jì)層面的廉價(jià)房屋集中化、[2][3]社會層面的種族身份的認(rèn)同[4][5]以及相關(guān)住房政策的影響[6]等。
國內(nèi)相關(guān)研究表明,外來人口分布的決定因素可以是社會、經(jīng)濟(jì)、歷史或自然環(huán)境等因素,或是它們的組合。[7]經(jīng)濟(jì)方面,地區(qū)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水平、產(chǎn)業(yè)結(jié)構(gòu)、房價(jià)水平、工作(如就業(yè)機(jī)會、就業(yè)率)及居民收入水平等都可作為影響人口空間分布與區(qū)隔產(chǎn)生的重要變量;[8]社會方面的原因包括城市交通及公共設(shè)施布局(如醫(yī)療、教育資源)、人口流動(dòng)、城市改造和居民心理因素等,其中社會區(qū)隔的產(chǎn)生與社會分層密切相關(guān),同時(shí)對低收入群體、社區(qū)和社會發(fā)展都產(chǎn)生影響;[9]政策方面引起社會區(qū)隔的原因包括城市規(guī)劃導(dǎo)向和不合理的住房政策等。
許多學(xué)者對于北京、上海、廣州等特大城市的外來人口聚居現(xiàn)象展開了深入研究,對本文研究有一定啟示。研究表明:首先,在空間集聚特征方面,上述特大城市的外來人口通常因?yàn)榉孔獾土⒔煌ū憬莸仍蚣性诮紖^(qū)[10]和遠(yuǎn)郊區(qū)縣政府駐地;[11]從城市發(fā)展過程來看,常住外來人口在向城市功能拓展區(qū)和城市發(fā)展新區(qū)集中。[12]其次,外來人口空間集聚的影響因素包括產(chǎn)業(yè)發(fā)展、就業(yè)崗位、住房供給及其成本、開發(fā)建設(shè)、政策管理、公共資源布局、個(gè)人收入、移民身份、地緣關(guān)系與社會資本等;[13][14]最后,外來人口的流動(dòng)和空間集聚是形成特大城市次中心和多中心城市空間結(jié)構(gòu)的主要?jiǎng)恿Α15]
從上海市相關(guān)實(shí)證研究來看,系統(tǒng)開展外來人口的時(shí)空演變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仍顯不足。由于數(shù)據(jù)可得性問題,目前最新可比數(shù)據(jù)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(shù)據(jù)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(shù)據(jù)(由于2015年1%抽樣調(diào)查并不對鄉(xiāng)鎮(zhèn)地區(qū)進(jìn)行全覆蓋),本文基于上述數(shù)據(jù)對上海市外來人口空間集聚的特征及其影響因素進(jìn)行初步討論。
二、上海市外來人口的空間分布及其演變特征(2000~2010年)
(一)總量規(guī)模及其演變
從總量規(guī)模來看,2000年上海市外來人口387.1萬人,2010年增至897.7萬人,增長了1.32倍,2000~2010年外來人口集聚地區(qū)總體上呈現(xiàn)出自中心向外圍圈層式擴(kuò)散的特征。2000年外來人口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區(qū)邊緣的近郊地區(qū)及外環(huán)線周邊,距離市中心10~30公里左右的范圍內(nèi);2010年外來人口集聚的地區(qū)從近郊向遠(yuǎn)郊地區(qū)擴(kuò)散,且呈現(xiàn)由內(nèi)而外圈層式遞減趨勢,距離市中心15~40公里范圍是外來人口分布最為集中的地域②,而中心城區(qū)和郊環(huán)線以外地區(qū)外來人口分布相對較少(圖1,圖2)。